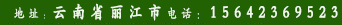|
7月13日至16日,第十四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来自世界近二十个国家、两百多位作家和学者齐聚丽娃河畔。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是由世界短篇小说研究会组织召开的一个国际性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是目前专题研讨短篇小说的唯一的国际性盛会。 7月13日下午,第一次全体大会暨中外作家对谈活动在华师大举行。中国作家苏童、余华、毕飞宇、赵玫、方方,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新西兰作家杰克·罗斯、爱尔兰作家伊芙琳·康伦、加拿大作家马克·安东尼·贾曼就“短篇小说中的影响和汇合:西方与东方”展开交流。 “我是短篇小说的儿子” 为了把短篇小说谈好,先来谈长篇小说,我写长篇小说最大的体会:它就是我的“爸爸”,年纪可能八十多岁了,把我养到五十多岁,我必须做的事情就是赡养老人,孝敬老人。我是用为他服务的心来面对长篇小说。每当我写短篇小说的时候,非常不幸的是,我同样认为短篇小说是我的“爸爸”,我是短篇小说的“儿子”,一个还在读高中的儿子,父亲是一个壮年的男人,是他哺育、滋养我的。 也许我写的一些长篇,给我带来了声誉和收益,未来人们记住的是我这几个长篇。但实际上我所有的能力,在文学当中被发现,是因为有短篇小说帮助我,哺育我,滋润我,让我一点点看到小说内部的那些东西,比方说短篇小说的人物,短篇小说的结构,短篇小说的节奏,短篇小说的简约,短篇小说的精准,短篇小说的生动,尤其是短篇小说的留有余味。正是在短篇小说的操作过程当中,我成长起来了。我有了骨骼,有了肌肉,让我有能力滋养我的另外一个“父亲”,所以最要紧的东西是准确、简洁。 ——毕飞宇 我这个年龄层的作家,一开始都是以写短篇小说开始的。慢慢写了很多短篇小说之后,突然中国有了一种新的形式叫做中篇小说,我后来觉得中篇小说容量更大,更能让我尽兴,便大量地写中篇小说。苏童写短篇小说写得多,有一段时间他们说我是中篇小说之王,苏童是短篇小说之王。 我觉得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会让我尽兴,我写作的时候会很喜欢这些内容,我热爱他们,就希望他们的事情越来越多,就越写越长。我们写短篇小说经常会点到为止,就像人谈恋爱,可能写长篇小说是西方化的恋爱,写短篇小说是老式中国人的恋爱,很含蓄——话到这里为止,你自己去猜——是更收敛的情绪。可能我写短篇的时候就会很节制,把话说到一半,不说透,而在写中篇或者长篇小说的时候,我会热烈奔放,把我想写的都写出来。特别是写长篇小说,一件事情发生另外一件事,每个人都像一个树的骨干,发出很多枝桠,可是写短篇只让一个枝往上走,不会让它更多的关系发展。我写短篇会找一个非常好的点,可以让它更节制更收敛。 ——方方 “翻译小说让我获得了比较正常的小说观” 关于东西方文学交汇和影响,每个人身上发生的方式和故事不一样。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接触真正的美国文学,是高中时代,我在苏州的新华书店用六毛八还是七毛八买了一本美国当代小说集。这个小说集当中,给一个爱好文学的高中生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两篇,一篇来自福克纳,非常不福克纳风格的小说,《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还有一篇是《伤心咖啡馆之歌》。其实这个集子里有很多好小说,奥康纳的《好人难寻》等,都是非常好的小说,后来想想,太奇怪了,为什么对那两篇小说念念不忘。 这两篇小说都是写美国南方,有一点哥特式味道,两个故事主人公都是老处女。我是通过文学接触到美国也有“南方”这个概念的。小镇,穿黑裙子、包得严严实实的老处女,夏天木板都要钉住,这是我想象的美国南方——一个来自中国南方,爱好文学的高中生,对美国南方的想象来自于这两篇短篇小说。而这两篇小说真正教会我的,是发现小说一定要写人物,人物跟意识形态完全是反的。那次阅读让我很感激,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催生,让我获得了比较正常的小说观。 ——苏童 80年代我接触的是更古典一些的外国作家,莫泊桑,海明威,梅里美。我第一篇小说的名字就是《羊脂球》,跟莫泊桑小说完全同名。这些外国小说使我突然对人性有了认识,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写小说仍然在写跟人性有关的东西。我的第一篇小说,就是《羊脂球》,也是写人性的黑暗,虽然故事不一样,也是写一个人帮助了很多人,最后他要承担所有的结果,而受他帮助的人都不站在他的立场说说话。这篇小说被当年的《长江文艺》退了稿,说你小说的结尾太不好了,我的老师也批评了这个小说,他说了一个词:“黑暗”,你的小说结尾太“黑暗”了。我写的就是人性当中很黑暗的一面,但当时并不知道小说还可以用这样一个词形容。多年以后,我把他改头换面,又重新发表了。 我们最早接触的一些作家作品,像雨果、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等,可以数出很多,他们对我们有强大的影响,我们就是读这样一些作品成长起来的。相信一个中国作家读过西方的文学作品,比一个外国作家读中国的文学作品要多得多。我们这代人可能就是在大量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当中成长和发育起来的,这是我们写作中的营养,也是我们人生成长的营养。 ——方方 “会有几个人和你的生命是契合的” 我是年到年读大学。当时比较较热门的几个人,首当其冲的是弗洛伊德。一个乡下的孩子,到了读大学的年纪,满眼看到的都是现实,突然有人告诉你,还有一个现实,在你的内心——这个东西挺吓人的,不仅仅是吓人,是让人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个可看的地方。另外一个比较热门的人物是柏格森,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直觉。以往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判断,通过逻辑、概念分析,在理性上做出一个结论、一个判断来。但是柏格森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可以跨过逻辑,然后直击你面对的对象。对一个小说家来讲,直觉是特别要紧的一个东西。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拉康,他的镜像理论告诉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认识了自己,可是怎么认识的呢,人是像看镜子那样,从别人对你的评判当中获得的自我认知。另一个热门的可能就是罗兰·巴特。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学是偏于抒情的,尤其是作家,动不动把自己的情感拿出来,作为推动小说的力量。可是如何才可以真正看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一个作家能不能做到罗兰·巴特所说的“零度”,有一个事情是真实的,我写作的时候比较多地在控制情感。 ——毕飞宇 我一直觉得,其实在写作当中,你用不着看很多书。会有几个人和你的生命是契合的,他们的东西像你自己的东西一样。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三个作家,一个是福克纳,一个是伍尔夫,还有杜拉斯,在我写作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像影子一样,无论我在什么样的地方,都会感觉到他们的存在。我写作当中始终是这样一种状态,你用不着看很多书,我自己这样觉得,读很少很少的一些作家,但是这些作家,要不停地读。 ——赵玫 ——根据网络资料整理 阅读链接生活看似趋同,短篇小说仍未穷尽可能性 眼下,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经验正变得越来越趋同,不少中国人也热衷过圣诞节,中外不少家庭的幸福感与焦虑感是相当重叠的,那么,以偶然性或出人意料见长的短篇小说,施展空间会不会被压缩?昨天在沪举行的第14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上,苏童、余华、毕飞宇、罗伯特·奥伦·巴特勒等中外知名作家围坐展开交流。 在不少小说家看来,短篇小说的多元化表现各有千秋,包含了寓言构架、直白描述、超现实勾勒等,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是,短篇小说具有的画龙点睛的神奇,来自对人性深处的探索。从曾经的出版冷门,到如今国内引进“短经典”系列、原创“华语短经典”系列的陆续面世,都预示着这一文学样式正在不断回暖,在与会的中外名家看来,短篇小说的艺术魅力仍未穷尽它的可能性。 从传奇到日常,短篇的艺术密码几经更迭 经过无数作家的笔下流转,短篇小说的魅力折射出不同的切面,其艺术密码几经更迭。短篇小说究竟是变得更传奇,还是愈发家常? 会场上,有小说家谈到,19世纪的短篇小说多是传统情节加上奇特事件与象征写法,渲染戏剧性、传奇性,写各种偶然与巧合的故事。比如莫泊桑《项链》、欧·亨利《麦琪的礼物》等,都在最后一刻上演剧情逆转。 到了20世纪上半叶,短篇的内容情节从奇特惊人悄然转向普通日常。苏童谈到,往历史深处追溯,不管是《十日谈》,还是“三言二拍”,都是根据市井生活编造了大量世俗意义上的故事,洞悉人生百态。在契诃夫、曼斯菲尔德、乔伊斯和安德森的手中,短篇小说成为一种表现日常生活经历的手段。契诃夫有个短篇叫《捉弄》,讲一个喜欢捉弄人的男孩带一个女孩滑雪,胆怯的女孩在风里听到一句“我爱你”,要求男孩“让我们再滑一次雪橇”。后来女孩爱上了滑雪,甚至开始克服恐惧一个人滑雪,再后来男孩走了女孩嫁人了,那句“我爱你”成了一个谜,因为男孩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捉弄,还是风发出的声音。于是这个世上最天真的爱情,都停留在风里。看似云淡风轻,寥寥数千字却写出了两性关系中的试探、遗憾与甜蜜。 20世纪50年代后,卡夫卡、博尔赫斯等作家信手拈来的超现实主义写法,一下子意味又变得多重和耐人寻味,他们发现“现实”世界的真实性是不可靠的,在他们变幻莫测的短篇里,现实与幻想咬合紧密,两者的界限几近消失,文字转向了游戏、技巧、嘲弄和自我嘲弄。比如,博尔赫斯喜欢在捉摸不定的叙述中一步步逼近一个完整而又耐人寻味的结局。不管是《釜底游鱼》结局里“苏亚雷斯带着几近轻蔑的神情开了枪”,还是《死亡与罗盘》结尾处“他倒退几步。接着非常小心地瞄准,扣下扳机”,都让故事戛然而止却又余味袅袅。 不少作家都倾向于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短篇小说家与作品》里的说法,在布鲁姆看来,有几种不同的短篇艺术密码:有的是去追寻真实,比如契诃夫;有的是去翻转真实,比如博尔赫斯。 从西方到东方,人性深处的颤栗是短篇的心跳 不同地域、种族、环境中的人们都会遇到的人生命题,在不同国家作家的笔下被表现得异彩纷呈。不过,眼下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经验正变得越来越趋同。 “这种变化对东西方作家的挑战是一样的。”曾获普利策小说奖的美国著名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告诉记者,他始终最想通过短篇小说释放的深层写作欲望,是在作品里梳理寻找“自我认同”,也就是最逼近内心的追问———我是谁?我属于哪里?他认为对这种人性深处颤栗的探索是全球共通的。巴特勒想了想,吐出一句总结:最好的短篇小说都是关于最黑暗的记忆。这种黑暗,不仅仅是困境或悲苦,更意味着人性在复杂生活漩涡里艰难地打转,而这种打转往往是不为人所熟知,是隐匿在暗夜中的。 不难发现,对现代人精神家园的寻觅、重构的书写,正是近年东西方短篇小说共同北京治疗白癜风费用是多少北京治白癜风的专科医院
|
大家说nbsp方方苏童毕飞宇
发布时间:2016-12-13 4:58:30 点击数: 次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温馨提示花都电台请您一家大细去滑雪
- 下一篇文章: 滑雪装备防弹衣nbspXION护